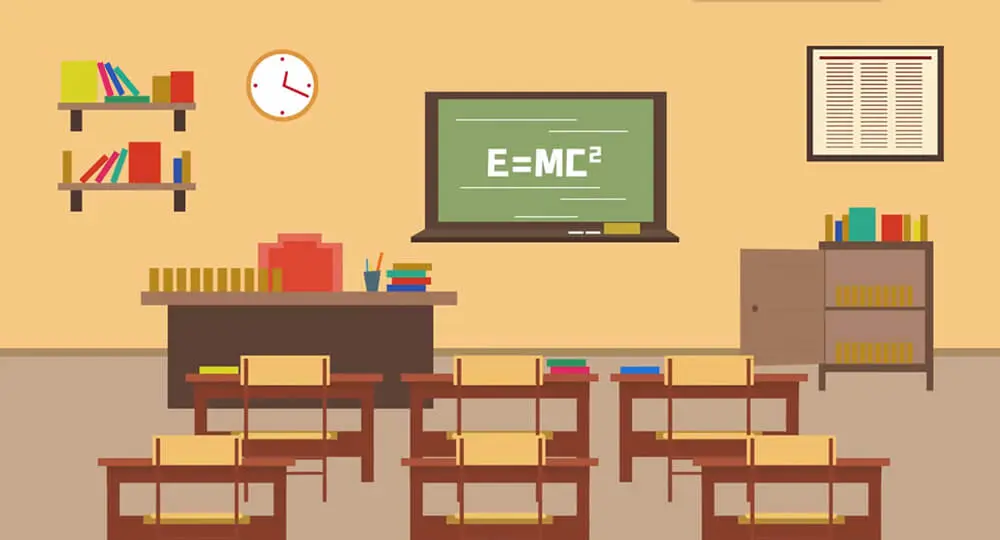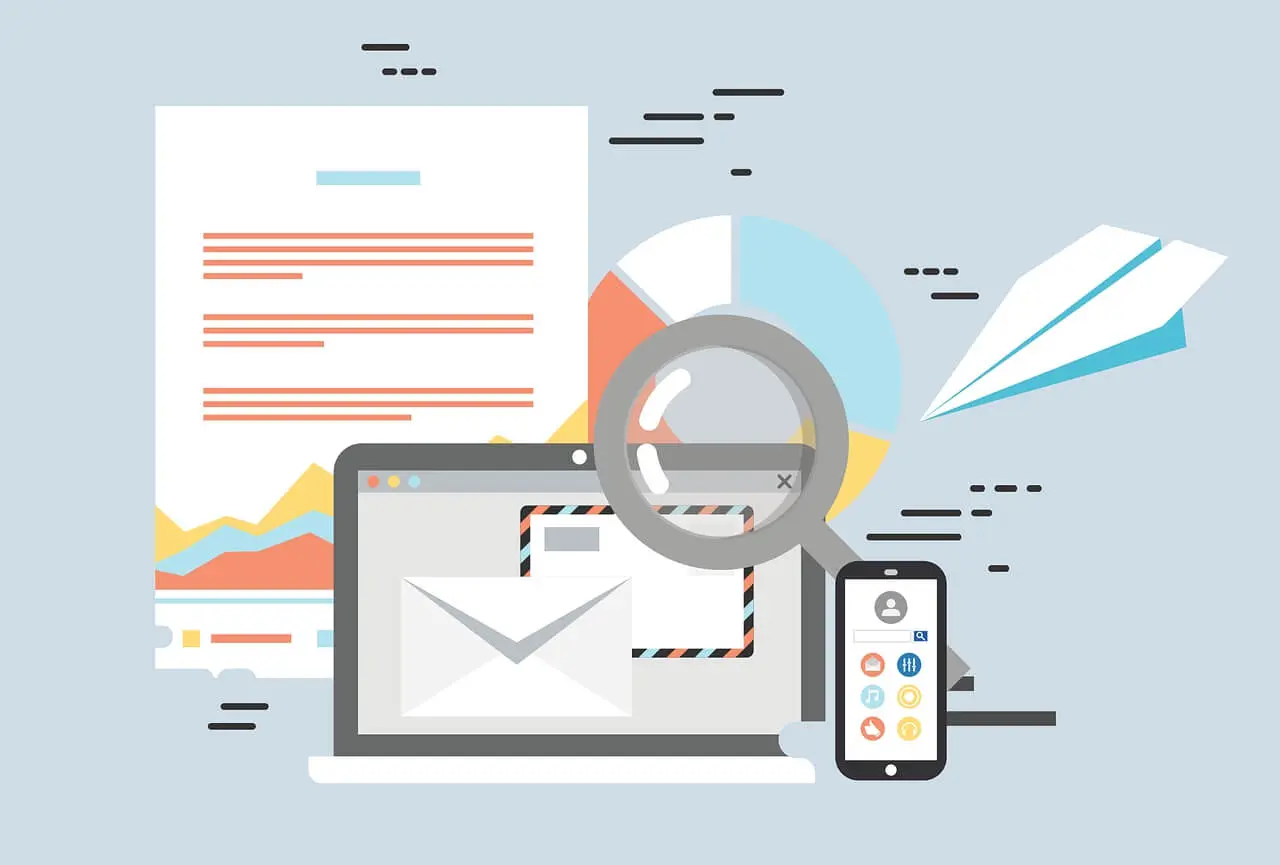锚点111
他曾怀揣着像偶像那样年少成名的梦想,然而在岁月的悄然流逝中,“神童”的光环逐渐离他远去。青春一去不复返,遗憾时常涌上心头,可他对写作的那份渴望却从未熄灭。
年轻时,他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宏伟的目标。二十出头的时候,他在自家书桌前挂了一张自制的时间线,用尺子和专业绘图笔,认认真真地从18岁画到30岁。他剪下了自己喜爱的作家的照片,贴在他们出版首部小说的年纪旁边:21岁的布雷特·伊斯顿·埃利斯、24岁的马丁·艾米斯、25岁的迈克尔·查邦和扎迪·史密斯、26岁的菲利普·罗斯、27岁的约翰·厄普代克。他还剪下了自己的脸,贴在了这群偶像中间。每逢生日,他就挪动一下自己的位置,期望每年都能超越一位偶像。
这些作家曾经都是光芒四射的年轻才俊,他一心想要追随他们的脚步,成为那样的“天才少年”。对他而言,写书本身倒不是最重要的,关键是要在超乎寻常的年纪完成——成为神童,惊艳众人,这才是点燃他野心的火花。在青春那模糊的瞭望塔上,他认定,如果30岁之前没能出书,那就是人生最大的失败。
然而,他并没有成功。30岁来临了,31岁也过去了,那张剪纸头像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。
年轻时做事,似乎走上了一条通往伟大的捷径。做对了,就证明你潜力无限;做错了,也不过是经验不足,时间会帮你慢慢修正。19岁时写了句烂话,没人会在意,毕竟还年轻。可45岁再写出烂句子,人们就会皱起眉头:这年纪了,怎么还不会写?于是,不再年轻的作家陷入了两难境地:妙笔生花不再是奇迹,而变成了基本要求。约翰·厄普代克36岁写出《夫妇们》,被奉为杰作;72岁写的《村庄》同样出色,可人们只会说:“当然好啦,毕竟是写《夫妇们》的他啊!”
岁月一点点地侵蚀着你的容错空间,直到一丝不剩。年轻时,错误只是经验的小瑕疵;后来,却成了性格的污点。青春仿佛永远站在完美的边缘,好像再努力一步就能到达,可你始终未曾抵达,转眼间就已老去,只能带着永久的不完美挣扎着面对现实。
他在25岁前写完了两部小说,可都没能出版,也算不上“好”。那完全是典型的年轻人作品:用力过度、自我意识膨胀、粗糙又骄傲,模仿着那些天才作家的风格,却远远达不到及格水平。其中一部讲了一个七岁男孩在课堂笔记本里写科幻惊悚故事,被老师发现后跳级,然后遭遇了成长小说里常见的桥段:霸凌、暗恋等等。多年后他才明白,这个故事赤裸裸地映照出了他的野心:渴望因为年轻而被认可,不是具体的成就,而是取得成就时的状态,那承载了他所有的骄傲与希望。
然而,那种状态已经过期了。他不再年轻,不再是“年轻作家”,自然也就成不了“杰出的年轻作家”。
即便如此,那个目标依然顽强地存在着,违背逻辑,无视现实——他还是想成为被人发现的年轻作家。只是,谁会去“发现”一个45岁的人呢?45岁不是被发掘,而是被揭露,就像有毒废料、政治丑闻,或者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里的凶手。天啊,原来这个45岁的老家伙一直藏在我们中间!
青春逝去后,他开始阅读关于二战、古希腊、美国内战、量子物理和宇宙历史的书籍,试图在世界的浩瀚中寻找慰藉。人到中年为何会迷上历史呢?或许是意识到自己被困在了时间的狭缝里,只能窥见历史的一角。就像生活中的一切,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触碰世界的范围越来越窄。所以退休老人爱旅行吗?那些在大巴上的老人们,步履蹒跚,一步步侧着脚走下车,只为了匆匆探索20分钟的古迹,是想在世界被夺走之前,再多看一眼吗?
年轻时度假,他满脑子都是憧憬。每到一个地方,他都想象自己能够留下来,开启全新的生活。在墨西哥、香港、法国、意大利,甚至印第安纳西部,他总是想:我可以在这儿生活,遇见一个女人,成家,融入当地。后来,他遇到了最好的女人,选择了最好的地方,未来就此定格。世界依然美好,可不再充满无限可能。那空缺的部分,又该用什么来填补呢?
年轻时,他幻想能遇见偶像,在咖啡店排队时鼓起勇气拍拍他们的肩膀,结结巴巴地说他们的作品对自己有多重要。在幻想中,他永远年轻,永远是潜力股,藏着惊艳世界的可能性。可如今,他老了,只能想象自己在Au Bon Pain排队,泪眼汪汪地向扎迪·史密斯倾诉崇拜之情——她只比他大三岁,这场景该有多尴尬啊!一个45岁的人这样献媚,实在是太可悲了!
不再年轻,大多时候就是这种感觉:可悲又可厌。
想起青春,你或许会想到12岁时攒零花钱买了一盘二手的《沉默的羔羊》录像带,看开头字幕时的心情。那一刻无比清晰:秋天,克拉丽斯·史达琳穿着灰色运动服跑过联邦调查局训练营的树林,画面渐渐褪色,黑色字幕配上低沉的音乐。年轻时,看着这一幕,你百感交集,想象着无数种未来。体内涌动着你将要写的连环杀手故事,未来会拍成这样的电影;视野之外,成人世界那些未知的细节隐约可见,你会遇见穿运动服的野心勃勃的女性,甚至娶她们为妻。那一刻,你是年轻的,无所不能。
可如今,你在纽瓦克出差的酒店里再次观看这段,感觉完全变了。它成了你没写成的故事的象征。你知道写故事有多难,知道托马斯·哈里斯写原著时有多痛苦,他在键盘前受尽了折磨。你害怕自己也会如此,无法享受写作的过程,只剩下对欢乐的愚蠢希望,就像彩票中奖一样渺茫。你甚至会想到改编剧本的泰德·塔利,拿了奥斯卡之后就再无建树,他如今在哪里呢?你遗憾没有机会见到他,那些经典台词如今也不常被引用了——文化也有青春啊。你还会惆怅那些没遇见的野心勃勃的女性,或者遇见了却没能打动她们,她们误解了你的好意,看不出你和她们一样:有点男子气概,充满抱负。
他最终在37岁生日那天出版了一部小说。比厄普代克晚了十年,比艾米斯晚了十三年,比埃利斯晚了十五年。处女作总是带着青春的气息,他的也不例外。但37岁写书并不会给你加分,没人会因为你的“早熟”而惊叹——不过是37岁写的另一本书而已。不算差,或许还行,但绝称不上伟大,不然怎么会拖到37岁才出版呢?
可你不只是在悼念自己的青春。后来有了孩子,他们的青春也在渐渐流逝,就像破胎漏气一样,又像在沙发后找到的派对气球,无声无息地瘪掉。你把小了的雪服送给邻居时会莫名地哭泣,得知配偶捐了睡前读的绘本时会无名火起。在4岁女儿的芭蕾演出上,看着她小小的身影在台上甜美地踉跄,你突然被未来淹没——她们将要经历的喜怒哀乐、自我厌弃与蜕变——胃里涌起一阵悲伤,这和读宇宙历史时的渺小感相反,那是一种近乎恐惧的情绪:青春的存在,似乎只是为了被摧毁。
他37岁出版的小说不算成功,但写作的冲动从未停止。那不是虚荣,而是天性使然。即便不想写,他也会在脑中构思段落、小说,用语言的影子和色彩拼凑出各种可能性。他活在书里,也想象着别人活在他的文字之中。这是他唯一懂得的亲密方式。
渴望被看见、理解、欣赏,并不只是年轻人的专利。你以为欲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褪去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你始终清楚前路漫漫,渴望让这一切变得有意义。傻梦只有在未实现的时候才显得可笑,而在放弃之前,它们都不算傻。
青春被慢慢剥离,他成为了现在的自己,继续挪动那张剪纸脸,就这样活完这辈子,直到生命的尽头。
本文译自Tolstoyan,由BALI编辑发布。